受陈徒手老师之约,要我写写正在写作中的《燕大史》的过程,遂草此文向陈老师交稿,也向关注我的读者们略作交代。——陈远
前不久,文道兄在《开卷八分钟》用了两期的篇幅推荐拙作《消逝的燕京》,让这所已经沉寂多年的大学再一次受到世人的关注。不过,让我稍稍不安的是,那么薄薄的小书,尽管受到读者过多关注的目光,却只是我为目前撰写的《燕京1919——1952》所作的前期准备,它所表现的,只是燕京大学不同时期的横断面,远非这所大学的全貌。过多的称赞,让我感到不安,也感到压力。
说十年磨一剑,似乎有点夸张,但从写作《教育家司徒雷登》一文到现在,倏忽已经十年。十年间,并非只关注于燕京大学,不过十年来所有的关注,似乎都在为目前撰写这本书做准备。
十年间,关于历史的观念有所变化,但是这个写作目标却没有改变过,我想描绘出燕京大学三十三年历史的全貌。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这似乎是过去的大学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是当下大学史研究最后的指向。这固然没错,不过,这其中,也包含了过多研究者的情怀,但历史的演进,不尽如此简单,当我深入的进入燕京大学的历史时,对于这一点有了更深的感触。
所以在这本书中,不想讲大道理,尽管燕京大学的发展也验证了没有学术自由却还想打造一流大学只能缘木求鱼这一事实。我想做的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搜集因为诸多原因而支离破碎的燕京碎片,拼凑出一张完整的燕京全景图。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以往关于燕京大学的研究著作不是没有,但是其研究主体,多是围绕着创办这所大学之后又被领袖否定了司徒雷登,除了由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编撰的《燕京大学史稿》、由台北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以及西方学者Philp West的著作《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m Relation 1916-1952》(《燕京大学与中西方关系》),之外,鲜有以燕京大学为研究主题的著作。《燕京大学史稿》更多侧重燕京大学各院系和学生的历史,《学府纪闻·私立燕京大学》则属于零星回忆性文章的汇编,《燕京大学和中西方关系》则是选择了国际关系的视角,而我关心的是,燕京大学自身演变的轨迹,以及它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政治史乃至社会史中发挥的作用和位置,之前的著作,给我提供了帮助,却不能完全解答我的疑惑。关于1952年院系调整这一运动中燕京大学遭遇,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之中更是语焉不详。这样的空白,给了我研究的动力,但也增加了难度。
尽管燕京大学是出了名的完备保存其发展的档案,但是由于诸多因素,查看这些档案,却出于意料的困难。我去过教育部的档案室,结果被拒之门外;去过北京大学的档案馆,结果被告知:“只有经过校长的批准,才可以查阅燕京的档案”;去过北京档案馆,结果关于燕京的档案大多数都被标注了“不开放”,没办法,我只好调整方法,放弃主要依靠档案的想法,采用主要依靠当事人口述、档案辅助的方式,尽管依靠档案是做研究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像是柳暗花明,当一扇窗被关闭时,另一扇窗必会开启,在走访健在的燕京老人的过程中,尽管时隔多年,我却发现他们关于燕京的记忆是那么鲜活,那些远久的往事,仿佛就像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我也惊诧于这些老辈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小辈的热情:侯仁之老不顾望百高龄,执意要带我在燕园中感受当年的环境;原驻美参赞 国仲元老师,虽然因为入学晚而谦称不够资格对我谈燕京的历史,却频频为我的访问穿针引线和为我提供燕京校友的最新动态;刚刚去世的周汝昌先生,得知我在做燕京人口述的工作后,主动打电话约我去他的寓所畅谈;从来不接受访问的谢道渊先生(当年院系调整的见证人之一)为我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每年四月燕京校友的返校节,老人们都不忘通知我参加;每期的《燕大校友通讯》,尽管这些年我几经更换单位,但总能及时寄到我手里……我想,这里面,一方面是我的挚诚打动了老人们,另一方面,不用讳言,也有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多年压抑——燕京的历史,在多年之中,曾经是燕京人心中彼此心照不宣的禁忌。
我渐渐感觉到,原本支离破碎的燕京史,开始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尽管还有一些资料无法穷尽,但可以动笔了。
另外要感谢铁葫芦图书总编辑王来雨兄的邀约,如果不是他,以我疏懒的本性,这个计划可能还会晚一些才会完成,是来雨兄的催促,使得计划提前。希望可以向来雨兄和多年关注我的读者们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尽管还在写作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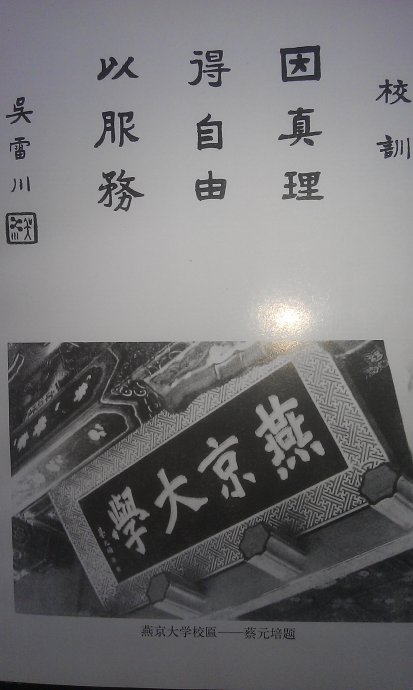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